我為什麼要寫川藏公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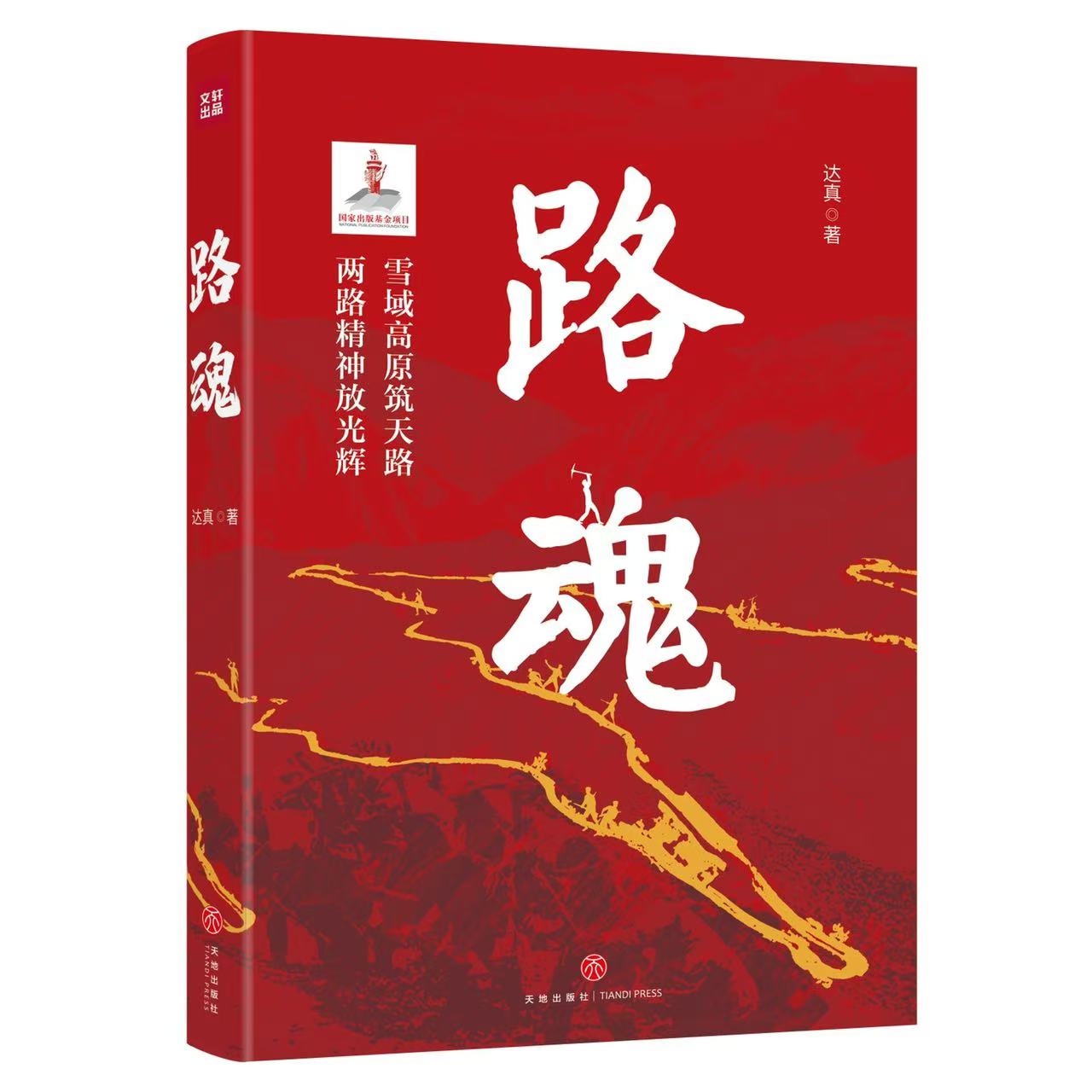
作者供圖
紀念川藏公路通車七十周年、“兩路”精神十周年之際,我的33萬字的長篇報告文學《路魂》出版發行。該書被列為“國家出版基金項目”、2023年度中國作協重點扶持作品。
如何在川藏公路通車七十年的今天,用全新的視角再寫川藏公路,於我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回眸七十年,上世紀五十年代,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大西南塑路魂,誓言“把紅旗插在喜馬拉雅山上”。“蜀道難,蜀道難於上青天”,大詩人李白的慨嘆,道出人類用雙腿走出文明的艱辛與悲壯。將唐朝出蜀的茶馬古道與今夕川藏公路相比,新中國在世界屋脊不但創造了人類公路史的奇跡,也刷新了路文明的高度,關鍵在於延續著中華文明基因裡“精衛填海”“女媧補天”“愚公移山”的精神魂魄。因為,新中國在全世界公認地質結構最復雜的橫斷山地區,用鋼鐵般的意志完成了人類無法想象的壯舉。
寫此書的目的是在先期作家們的基礎上,從更加宏闊的維度,俯瞰川藏公路的前世、今生和未來:一是新中國剛成立不久,中國軍隊同時在朝鮮、在西藏保家衛國﹔二是第一次比較川藏公路和史迪威公路的興衰﹔三是從茶馬古道、孫中山川藏大鐵路計劃、劉文輝康藏公路,洞見隻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和人民才能完成這一偉大工程。以歷史和文學的手段描摹川藏公路的時代畫卷、文明畫卷、精神畫卷,展示“一帶一路”中國段的世界范式。
在動筆期間,我大量閱讀了紀念“兩路”精神十周年到六十周年的作品,除了被幾代作者用心血著述的文字所感動、所敬畏外,還必須脫繭“言者諄諄聽者藐藐”的壁壘,寫好中國故事,共享人創造進步的榮耀。此外,動筆前,我也一直提醒自己,針對川藏公路的書寫,務必站在“人類命運共同體”和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的坐標點和出發點,規避因紀念日而應景的泛泛而談,全景式地書寫七十年來,因“交通興則百業興”,這一“綱舉目張”所鋪展的豐碩成果。
四十年前,時任國務院副總理谷牧率團考察西歐,曾驚嘆於西歐的高速公路網,那時中國沒有一公裡的高速公路。當時西方主導的話語平台這樣描述中國,要實現夢想好比“讓航空母艦在硬幣上轉圈”。
四十年后,“人類發展史上最激動人心的例子超越想象”,改革開放正收獲來自國際社會的普遍贊譽,中國公路總裡程、高速公路裡程、高鐵裡程世界第一。
短短的四十年,中國交通奇跡,到底由什麼精神動力推動出如此巨大的能量?
答案在深入探尋中逐漸明晰:應運川藏、青藏公路而升華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頑強拼搏、甘當路石,軍民一家、民族團結”的“兩路”精神,在世界屋脊向世界濃縮了人類文明進步,而且成功走入百年大黨的“精神譜系”,成為中國人的精神豐碑。
川藏公路建成八年后的初冬,我降生在川藏公路重鎮康定,從小目染川藏線的車輪滾滾,之后三十四年有在川藏公路沿線的記者經歷,深度體驗了川藏公路的巨變。之后,常常把川藏公路、河西走廊,作為西藏和新疆與外界交流的原點,因為它們是集長城、古城、邊關等歷史文化遺產於一身的文明走廊,兩者的開放與封閉尺度與中國的興衰相關。
因此,川藏公路對於我有雙重含義:
它是具象的路,像一條穿越時空的哈達,鋪展在廣袤的青藏高原。從此,青藏高原以車、路、人之間的密切聯系,“萬花筒”般地呈現了川藏公路邁向中國式現代化的實景實績﹔
它更是一條精神的路,猶如投影在大地上的巨幅唐卡,細密地描繪出張國華將軍、譚冠三政委、張福林烈士、怒江十英烈、雀兒山五道班陳德華、時代楷模其美多吉等一座座精神的豐碑。雖英雄已遠去,但英雄們的精神、經驗、人品、人格所構成大寫的“人”字,與日月同輝,值得去書寫與講述。
如何打破“言者諄諄聽者藐藐”的危局,給世界講中國的故事?
改革開放的巨變提升了我的認知,認為書寫不能一味地沉浸在自己的文化敘事中自娛自樂,而是要大膽地突破信息繭房和自感舒適的同溫層,讓不同文化區的人知曉、理解、接受,分享與共享。
共享的端倪表現在二〇二三的春節,全世界華人區慶祝新春佳節之際,意大利、法國、美國、加拿大、英國等地的外國人大量涌入華人社區,中國文化潤物細無聲地潛入他們的興致中,他們舞獅子、跳秧歌、敲鑼鼓、揮扇起舞,充滿中國民俗的文化場面,讓我茅塞頓開。
孫中山先生曾說,“道路者,文明之母也,財富之脈也”。“交通興則百業興”的道理就在於共享共情同心。交通猶如一棵大樹的主干,它生發出密如蛛網的枝干,串綴了廣大農牧區,脫貧攻堅的偉大成果,在這個密如蛛網的體系內,惠及到每一個末梢,像春節分享給世界的舞獅舞龍,讓世界看到不一樣的東方文明。
這溫暖的光芒,何不用飽含理性而溫情的筆觸,像庖丁解牛一樣,把根植於“人民至上”的“兩路”精神結出的碩果分享給世界,照見中國勇氣和智慧。
順著這個思路分析新中國交通史,川藏青藏公路能冠以“精神”之名,為何寫進中國共產黨百年大黨的“精神”譜系,便會豁然開朗,不禁要問,是什麼力量在支撐這一偉大壯舉?
曾經因寫長篇小說三部曲《康巴》《命定》《家園》,游歷滇藏時,採訪過川藏、滇緬公路。奇妙的是兩條公路都誕生於世界最年輕、中國最長、最寬,兼有太平洋和印度洋水系的萬仞千壑的橫斷山地區。上世紀四五十年代的世界東方,橫空出現兩條改變亞洲的地緣格局的傳奇公路——“史迪威公路”和“川藏青藏公路”。
兩條公路,兩座豐碑,兩個經典,兩個傳奇。
史迪威公路開辟了二戰交通史的新紀元,體現出決策者的戰略眼光、格局和膽識﹔川藏青藏公路絕非僅僅開辟了新中國建設史上的新紀元,而是在平均海拔4000米、地質結構最為復雜的世界第三極,這個新中國“一號工程”,在沒有地圖和水文資料的情況下,解放軍和筑路民工用鐵錘、鐵鍬、鐵鏟,用生命和意志,硬生生在奇、難、險、峻、惡的世界屋脊,刨出一條保家衛國的生命血線,創造了世界交通史上最偉大的壯舉,同樣映照出決策者的戰略眼光、格局和膽識。
七十年后回看“史迪威公路”,曾經憑借雄厚的美元和先進技術裝備修筑的路,而今已是雜草叢生,布滿畜糞,不少路段甚至露出七十多年前鋪路的原木路基,隨二戰結束而結束,神龍見首不見尾。
反觀川藏青藏公路,七十年來從泥巴路、柏油路、高速路再到鐵路,其間建設和養護從未間斷,憑借國力不斷升級,成長為多聲部合唱的政治路、國防路、經濟路,文化路、旅游路,一路上照見著人民的奮斗之志、創造之力和實踐之果﹔成為鮮活的沒有圍牆的愛國主義、民族團結、“兩路”精神的教育基地、示范長廊﹔成為黨的十八大后舉世矚目的脫貧攻堅、鄉村振興的幸福路﹔更是“一帶一路”倡議給世界“命運共同體”的中國方案。
回眸川藏公路時光長廊,如何在“兩路”精神七十周年之際,拿出一部什麼樣的作品來緬懷英雄、激勵后人,用精神的火炬照見中國式現代化國家的奮斗途程﹔如何站在更高的維度,走出傳統宣傳的邊界,站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高度,去透視“兩路”精神的歷史意義、當下意義和未來意義?對寫作是巨大的考驗。
我試圖嘗試用更宏觀、更細膩的視角探尋“兩路”精神的肌理和脈絡。
一千三百多年前,當文成公主和鬆贊干布喜結良緣,便有了大昭寺門前漢藏一家的唐蕃會盟碑﹔當漢地的茶和藏地的馬在古道握手,便有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定名的人類大愛之歌——《康定情歌》﹔1906年,趙爾豐奏請朝廷在茶馬古道基礎上修建牛車道,足見其鞏固邊疆的戰略遠見﹔民國初年,孫中山提出“川藏鐵路事關中國國家安危存亡”的戰略設想﹔1948年劉文輝組織修建雅康公路,僅初通余月,最終擱淺。一朝接一朝的仁人志士,雖有雄略,憾有未盡事業。於是,從歷史的演進得出舉世勿爭的事實:在世界屋脊完成這一人類的壯舉,非中國共產黨莫屬。
文明的最終落點是人的進步,人的生命的價值體現在被重視、被認同、被肯定。社會的發展最終體現在人的發展。作為一名生於斯長於斯的高原人,驚嘆的不僅是川藏公路,更多是沿途的滄海桑田,是在此基礎上的全面升華,是公路沿線人的變化、人的素質的變化、人的觀念的變化、人的幸福指數的變化、各族人民同心跟黨走的變化。特別是新時代創舉出的脫貧攻堅、鄉村振興、“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青藏畫卷。
基於此,我分將三個部分來書寫《路魂》的內涵:一同構建精神的文化長城。
塑魂之路——書寫七十年來,以中國特色的模式亮相於世界民族之林﹔巨變之路——書寫七十年的發展,四個自信具足“以人為本”的發展理念﹔“一帶一路”——書寫多元文明,人類命運共同體是這個藍色星球的必由之路。
沒有偉大的文明就沒有偉大的國家,繼承這樣的文化遺產,才是真正的東方巨人。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 
- 評論
- 關注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