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列車”上有科幻迷“永不下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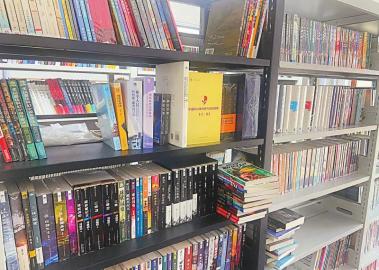
馬門溪龍科幻圖書館。四川日報全媒體記者 文露敏 攝
周四、周五的夜晚,四川大學江安校區的某間教室裡,通常會反復響起一個詞:科幻。
這是一節核心通識課,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中國科幻研究院副研究員姜振宇是授課的教師之一。作為國內首位“科幻博士”,他的課總能吸引大批聽眾。台下,來自四川大學科幻協會的幾位同學總是扎堆坐在一起。會長趙陽漾聽到激動處會站起來提問,甚至還會推薦起科幻小說。師生關系之外,姜振宇和趙陽漾都有一個共同的“標簽”:科幻迷。在趙陽漾看來,科幻好比一輛疾馳的列車,他們就是那些“不下車”的人。
在書架間,迷上科幻小說
從成都雙流的棠湖·泊林城小區1號門到94棟9號“馬門溪龍科幻圖書館”,需要路過許多長得一模一樣的小樓,左拐再右拐,再左拐右拐,步行用時大概是10分鐘。
圖書館館長華文的一部分工作,是拆開每天送來的圖書快遞,管理上萬冊科幻書。
因為開學忙著招新,趙陽漾已經有一段時間沒來這裡了。暑假前,她到“馬門溪龍科幻圖書館”的頻率最多時達到一周3次。
高三的時候,趙陽漾也擁有一間“科幻圖書館”。在學校為每位同學配備的衣櫃裡,她挪走自己的衣服,再用亞克力板隔出一個小書架,裡面放幾本書,供有興趣的同學翻閱。重點高中理科競賽班氛圍向來緊張,這裡是難得的“換氣口”。
94棟9號裡的科幻書,數量比1000個衣櫃裡的科幻書加起來還要多。去年搬到此處后,3層小樓很快被書架填滿,書架上的書又按年代和主題整齊碼放。因為空氣對流,哪怕有很多上個世紀出版、早已氧化變黃的“老古董”,也沒有預想中的氣味。華文幾乎每天都會打掃衛生。
二十多年前,他也是在這樣的書架間,讀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批科幻小說——法國作家凡爾納的《海底兩萬裡》、英國作家威爾斯的《隱身人》……
1999年,因刊發的文章與當年高考作文題“撞車”而“出圈”的《科幻世界》雜志,也在2000年經歷了印數接近40萬冊的“巔峰時期”。但在山東某小學一間小小的圖書閱覽室內,沉迷書中情節的華文還並不清楚,讓自己“入了迷”的書頁有一個共同的名字:科幻小說。
“先讀到一本喜歡的小說,記住作者的名字,發現他是科幻作家,再注意到原來很多書都屬於科幻。”姜振宇接觸科幻之初同樣懵懂。
哪怕頭頂“國內首位‘科幻博士’”的光環,姜振宇也是在書架間長大的“野孩子”:小學時,書架在縣城的新華書店裡,“父母上班時往那一撂,中午吃飯時再接走。”中學時,書架在回家路上的報刊亭,“一路問過去,最新的《科幻世界》雜志出版沒?”他因此認識了很多報刊亭老板。
科幻迷與科幻的故事,大多也是這樣開始的。
科幻是愛好,也是事業
締結姜振宇和報刊亭老板友誼的《科幻世界》雜志,是許多科幻迷繞不開的“白月光”。
2016年,腼腆的四川師范大學學生丁培富鼓起勇氣參加了科幻世界雜志社組織的一場活動。當時,科幻迷們聚在商場的影院門口,舉著牌子,為中國科幻大會拍攝祝福視頻。那天,丁培富結識了《科幻世界》雜志主編拉茲。
3年后,正是在拉茲的引薦下,剛從成都某媒體辭職的丁培富來到人民南路四段11號6層,成為了《科幻世界》雜志的一名編輯。
在科幻圈裡,這樣的事情並不稀奇。拉茲本人2006年入職雜志社,此前,他同樣也是《科幻世界》的鐵杆粉絲。
如果說,科幻迷們愛上科幻是源自最原始的感情——一種對未知世界的好奇、對宏大世界的敬畏,那麼,選擇科幻作為自己的事業,則是出自某種對中國科幻隱隱約約的積極判斷,甚至是“責任”。
2009年,整日“混跡”大學校園BBS的姜振宇,著手推動學校科幻協會的重啟。協會還沒有正式落地,他便在機緣巧合之下得到了一個機會,請科幻作家劉慈欣到浙江大學作講座。為此,姜振宇花光了兩個月的飯錢,租下了藝術系的某個“舞廳”作為場所。
當時,劉慈欣創作的《三體》已在國內科幻圈內成為一個“裡程碑”式的作品。那天,在迪斯科球和歡迎橫幅下,劉慈欣對著台下的同學們緩緩講起科幻。
2015年,劉慈欣憑借《三體》摘得雨果獎,“科幻”開始被更多人所知。也是在那一年,姜振宇開始攻讀國內首個“科幻博士”。“讀研期間經常到北師大蹭吳岩老師的課,接觸了很多西方的科幻理論,很想把這個事情講清楚。”而在早年間的媒體採訪中,被問到為何選擇讀博,他用了一種更肯定的回答:“為了一輩子做科幻。”
同一年,華文開始走上收集科幻小說、雜志的“不歸路”。那個時候,很多國家都有科幻圖書館、博物館,但這對積累了大量科幻受眾的中國來說還是“新鮮事兒”。
能發掘的科幻作品越來越多,華文前前后后一共搬了4次家,“書收集多了就要增加書架,書架多了就想著用更多的書填滿,隨著書和書架越來越多,就隻有換新家了。”
未來的兩三年,華文還想找到更多、更全的科幻作品。因此,棠湖·泊林城小區94棟9號,或許還不是最后的“家”。
一趟列車,有上有下
正在讀法學的趙陽漾未來或許並不會從事科幻有關的職業。“不過,科幻已經成了我的‘事業’。”說這句話的時候,時間正指向晚上11點,她和另一位同學正在討論科幻協會一場活動的宣傳文案。川大科幻協會有近千人規模,19歲的趙陽漾正在學習如何管理好它。
剛開始喜歡科幻的時候,她還好像身在一座“孤島”,舉目四望,沒有同行者。“這是從孤獨走向不孤獨的過程。”
科幻迷的圈子說大不大,華文就是這張“網”其中的一個連接點。在知乎“科幻迷有哪些特點,怎樣才能認識更多科幻迷”的提問下,有人開玩笑似的回答:科幻迷的共同特點是認識華文。認識更多科幻迷的最佳途徑是認識華文。
在“馬門溪龍科幻圖書館”,從擺放著懶人椅的一樓登上長長的扶梯,可以借閱的書集中在二層,書脊底端都被工整地貼上“借”字標簽。有科幻迷想要借書,不需要填寫登記簿,隻用微信上打個招呼。華文把它概括為“科幻迷之間的一種信任和默契”。
另一位活躍在圈子中的科幻迷叫河流,與其他人不同的是,他更像一個“科幻愛好者的愛好者”。在河流因急性心肌炎等疾病住院的2020年,是QQ群、微信群裡的伙伴們不斷給予精神上的慰藉,陪伴他度過那段與吊瓶和寂靜為伴的日子。
出於這份情感,河流開始對科幻迷這一群體進行曠日持久的研究,發表了《中國高校科幻協會簡史》《中國科幻迷雜志發展簡史》《中國科幻專業平台與粉絲平台的劃分》《中國科幻從業者對外國科幻的印象》等文章,並最終入圍今年雨果獎最佳粉絲作者。他主編的雜志《零重力報》,也入圍了本屆雨果獎最佳粉絲雜志。
河流觀察到,中國活躍的科幻迷群體集中在大中小學,而在國外,活躍的中老年科幻迷更多。剛入圈時結識的科幻迷朋友們,有很多已不再在群裡發言,仿佛一滴水滴入海洋,杳無音信。
丁培富曾在雜志社接待過一對來參觀的父女,看著興高採烈、問東問西的女兒,四十多歲的父親忽然感慨:“這裡感覺沒什麼變化。”原來,他也曾是一位科幻迷,大學時到雜志社參觀過。如今,這位父親為女兒訂了一整年的雜志,自己也會在工作不忙的時候翻幾頁,但再也不會完整閱讀一本科幻小說了。
面對離別,趙陽漾有些可惜,但也很釋然:“科幻就像一輛列車,有人在18歲下車,有人在22歲下車。”當然,還有一些人會一直在車上。
趙陽漾想試著做那個“不下車的人”。她始終認為,科幻就好像在叢林裡走夜路時撿起的那根樹枝,雖然不是真的“寶劍”,但也讓人擁有走過黑暗的勇敢。
就像一位協會成員曾寫下的感言:“科幻未必會成為我們一生的職業……但當你讀完一篇冒險的故事后,一定不會止步於此,而是會更加想要探索未知的世界……當你走向城市,閱讀的就是工業的文明,當你邁向荒野,閱讀的就是蓬勃的自然,當你飛向太空,閱讀的就是無垠的宇宙……”
無論在車上還是車下,逍遙的幻想永存心中。(四川日報全媒體記者 文露敏)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 
- 評論
- 關注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